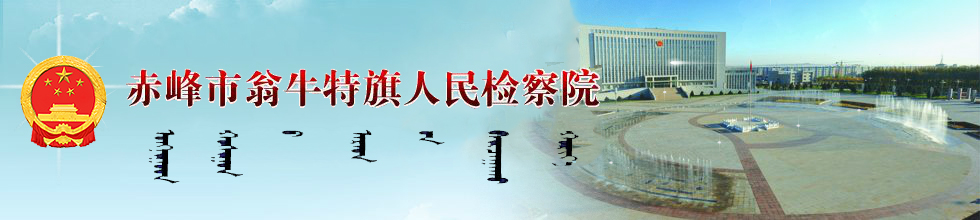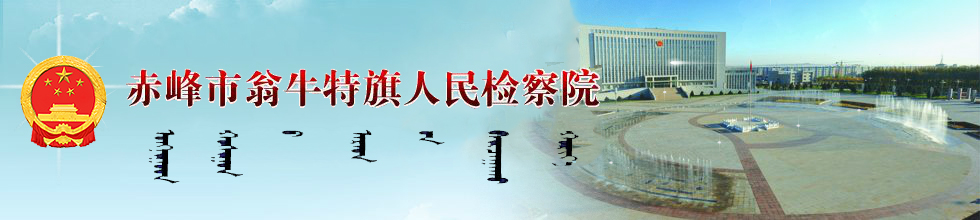盗窃罪法律适用问题预研综述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盗窃违法犯罪行为多发常见,数十年来曾长期占据我国刑事案件发案量和被追诉量的首位。自2013年两高发布《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来,已有十余年未有关于盗窃罪的立法或司法解释规定出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现实社会生活的不断变迁,盗窃犯罪理论与司法实践不断面临新问题、新挑战,无论是现行立法中传统定罪模式法律适用的理解与运用,还是信息化、数字化的网络时代下新型侵财行为的定性问题均存在诸多分歧。
四川省院研究室组成工作专班,对盗窃罪法律适用问题开展调研,查询梳理了检答网中北京、辽宁、浙江、山东、广东、四川、陕西等七个省份1300余条关于盗窃犯罪的咨询问题,归纳总结出较为集中的争议性问题有盗窃次数认定、数额计算,盗窃罪与职务侵占、诈骗等其他犯罪的区别,第三方支付平台侵财的行为认定等。结合调研情况,形成以下观点综述。
一、“多次盗窃”的司法认定
(一)关于多次盗窃中次数的认定
《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关于多次盗窃的次数判断标准一直是困扰学界和实务界的难题,争纷主要存在于综合标准说内部。最高检指导性案例要旨指出,行为人虽然“多次盗窃”,但根据行为的客观危害、情节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等综合考量,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不应受刑法处罚的,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二)关于未完成形态应否纳入次数计量
在“多次盗窃”的讨论场域中,未完成形态是否影响次数的计量存在不同观点。从罪刑均衡出发,盗窃预备行为对公私财产利益造成侵害的危险性较小,在司法实践的现实做法上,盗窃预备行为是不受刑事追究的,不宜将盗窃预备行为计入盗窃次数。
(三)关于已受行政处罚的盗窃行为应否纳入次数计量
“多次盗窃”属于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衔接问题,学界与实务界对于在时限内已受或应受行政处罚的盗窃行为是否影响次数计算的争议不断,分歧点主要在于是否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刑罚与行政处罚属于截然不同的制裁手段,合并运用此两种手段,并不与“一事不再罚”的法律原则相抵触。先前的行政处罚非但不能成为减轻罪责的理由,反而成为揭示其持续犯罪倾向和深重罪责的强有力证据。在此情境下,将行为人定罪处罚,既符合法律原则,也顺应了社会正义的期待。
二、“入户盗窃”的司法认定
(一)入户盗窃的“非法性”认定
对于入户盗窃的入户目的需具备非法性不存在争议,但围绕该非法性的内容存在争议。入户盗窃作为盗窃罪的基本行为类型之一,其规范功能在于扩大盗窃罪的处罚范围(即将数额不大的入户盗窃行为以独立的行为类型入罪)。正确认定“入户盗窃”,需要结合行为人“入户”的目的、手段方法、入户与盗窃的紧密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二)入户盗窃的既未遂判断
入户盗窃的既遂标准存在一定的争议。入户盗窃属于财产犯罪,应以行为人取得财物为既遂标准,需取得刑法保护的财物才构成既遂。弥补入户盗窃未遂不罚的处罚漏洞,改变新型盗窃罪既遂标准未必是唯一选择。
三、“携带凶器盗窃”的司法认定
(一)对“携带”的理解与界定
“携带”要从以下几个角度理解。一是行为人的主观意思。是否要求“随身携带”,学界存在较大争论,“紧密控制”标准较为科学。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实质审核把握。
(二)对“凶器”的理解与界定
《盗窃罪司法解释》将凶器分为“性质上的凶器”和“用法上的凶器”。“性质上的凶器”指爆炸物、枪支、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用法上的凶器”指在使用方法上,可能用于伤害他人的器物。前者认定基本无争议,关键在后者,即何为“用法上的凶器”。对“凶器”的理解在学理上并无太多争议,“性质上的凶器”要以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为标准;“用法上的凶器”要结合行为人的使用意思(具体用途、使用可能性等)、物品杀伤机能的高低等要素综合衡量。
四、“扒窃”的司法认定
扒窃行为主要通过“公共场所”和“随身携带”来加以界定,其中对“随身携带”存在不同认定。扒窃与普通盗窃的区别在于还具有侵犯人身权利的潜在危险,也是其社会危害性更重的体现。因此,判断是否系随身携带,区别扒窃与盗窃,财物与被害人的空间距离固然重要,但不宜将物理空间距离作为评判是否系随身携带的唯一标准,应当结合行为对人身权利的威胁程度、是否侵入了他人的贴身范围进行综合判断。
五、盗窃数额的司法认定
作为盗窃对象的财物应当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而所谓经济价值应是指物品客观的、可以货币形式予以体现的属性,盗窃数额实质上是盗窃犯罪人侵害财物的货币数量或其他财物折算成的货币数量。但与外币、电力、燃气、自来水等财物以及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等可以明确计算或者大致推算价值的财物相比,普通财物常因缺少有效价格证明或因财物灭失无法进行估价导致盗窃数额无法计算的司法困境。盗窃数额计算方式要构建严密完整的“价格证明>估价>销赃价格>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计算技术体系,防止司法实践中因数额无法计算导致的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等争议。此外,盗窃罪数额标准,虽更多涉及刑事政策而非法律适用,但其作为惩治盗窃犯罪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既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群众收入增长情况,也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感、现实治安状况、刑罚适用总体趋势和与相关司法解释的协调”。
六、关于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的区别
(一)关于职务便利的认定
对职务便利作出广义解释更为符合法理,其合理性可以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各种解释方法获得确认,符合法益保护要求,也有利于避免“增加”被告人刑事责任而有利于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在法理上和刑事政策上均较妥当性。
(二)关于非法占有方式的认定
对非法占有方式作狭义解释,可以作为广义理解下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构成要件的限定,并将盗窃、骗取等行为排除在职务侵占罪的规制范围外,严格限定职务侵占罪的适用范围,实现与盗窃罪的准确区分。
七、关于盗窃虚拟财产的相关问题
(一)关于“虚拟财产”的理解
明晰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对象之性质,是研究其定罪量刑的前提,关键在于虚拟财产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学界主流观点持肯定说。但由于本身“虚拟财产”之外延并非明晰,有限肯定其“刑法意义上的财物”的属性,有利于在具体案件中灵活把握,实现罪刑相适应。在此,倾向于参考折衷说,将“价值属性”“占有和支配”等要素作为衡量标准。
(二)关于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的定罪
关于盗窃虚拟财产的定罪,主要集中在以盗窃罪还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定罪上存在分歧。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还是盗窃罪论处,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考虑:一是侵害法益。《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隶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为侵害公共法益行为;盗窃罪为侵害私人法益行为。对于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需要辨别受侵害法益的属性。二是行为模式。盗窃虚拟财产行为可能通过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方式实现,也可能通过传统的骗取、盗取账号密码等方式实现,不宜机械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三是量刑幅度。盗窃罪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法定最高刑为七年,相较于盗窃罪更轻。
(三)关于盗窃虚拟财产的数额认定
目前,实务界多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认定罪名,重要原因在于盗窃数额难以认定。绝大部分虚拟财产都有专门的交易平台且有相对稳定的价格换算规则,且出现了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意见的新型价值鉴定机制。建议在考察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机制是否成熟的基础上,确定是否采用“数额认定”作为情节判断标准,反之,可以参考部分学者意见,综合考虑行为的次数、持续的时间、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种类与数量、销赃数额等。
八、关于通过窃取他人第三方支付账户信息获取已绑定信用卡资金行为的定性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网络移动支付方式已经成为常见的支付模式,围绕第三方支付平台发生的侵财犯罪定性问题持续引起关注与讨论。其中,当行为人通过窃取支付宝、微信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信息而获取绑定的信用卡资金行为应当如何定性,该行为属于盗窃犯罪还是诈骗类型犯罪,在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存在较大争议。
一是关于实行行为是否具备“秘密”要素。二是关于第三方支付机构是否有处分行为、能否被骗。三是关于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信息是否属于“信用卡信息资料”。
九、利用智能设备、信息系统漏洞非法获得财物行为的定性
对于利用系统漏洞获得财物行为,虽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但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远轻于普通盗窃罪,不宜作相同处理。建议对于偶犯,数额未达到“数额巨大”的,可以不按犯罪处理。对于构成犯罪的,也不宜单纯以数额作为量刑情节,即便符合“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也不宜以此作为法定基准刑,可以通过数额减半、引入“是否主动归还”等情节,综合判断其社会危害性,避免量刑时出现偏离常情常理的过高基准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