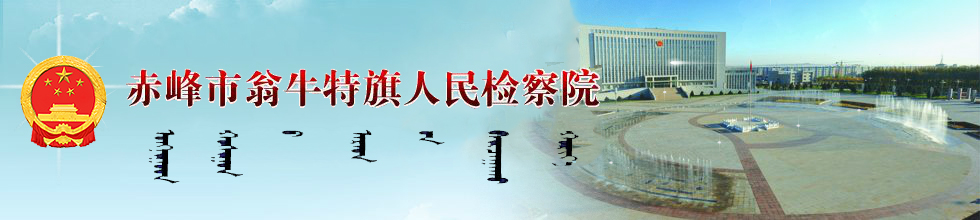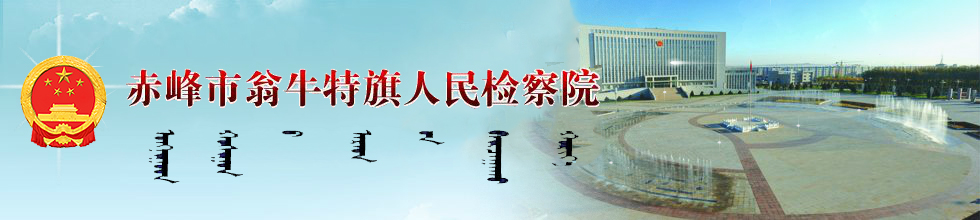关于加强涉未成年人案件行刑反向衔接
工作的建议
武汉大学行政检察研究基地教授秦前红等在其专题报告《关于加强涉未成年人案件行刑反向衔接工作的建议》中认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人数增多、比例逐年增高。基于这一现状,未成年人检察领域中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机制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通过行刑反向衔接做好不起诉案件的“后半篇文章”,避免未成年人案件陷入“不起诉等于不处罚”“一罚了之”或“一放了之”的困境中。为进一步规范涉未成年人案件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流程,检察机关可以考虑以司法文件的形式印发《加强涉未成年人行刑反向衔接工作的实施办法》。
一、提前研判机制
在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对于有必要提前研判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以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就是否需要建议给予被不起诉未成年人行政处罚等事项一并讨论。
当涉及疑难情况,尤其当需要与专门(矫治)教育制度衔接时,检察机关可以与行政主管机关及时沟通,听取其对被不起诉未成年人行政处罚的意见。由于专门(矫治)教育的启动与推进涉及多方主体,检察机关在制发检察意见的过程中,就是否适用专门(矫治)教育的问题,应加强各部门协作,强化沟通,全面听取教育部门、公安部门等多方意见。
基于专门学校建设的实际情况,当出现应予专门(矫治)教育而本地无条件提供专门(矫治)教育的特殊情形时,检察机关应当在征求教育行政部门、公安机关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并征得同意后,向异地教育行政部门、公安机关提出适用专门(矫治)教育的检察意见。
二、同步审查与全面审查的统筹
基于涉未成年人行刑反向衔接工作由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归口管理的组织特性,应统筹完善同步审查与全面审查机制,合理确定涉未成年人案件审查标准,综合考虑基本案情、不起诉事由、案件事实及证据、强制措施、量刑情节、处罚时效等内容,以及是否存在行政违法行为、是否应当进行行政处罚、是否已经受到行政处罚、是否已经达成和解协议或已经赔偿等要素。
三、规范制发检察意见
对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经未成年人检察部门讨论决定,对被不起诉未成年人提出建议给予行政处罚或专门(矫治)教育的检察意见:(1)尚未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证明存在违法事实的证据确凿;(3)作出行政处罚或专门(矫治)教育决定的法律依据明确;(4)未超过行政处罚时效;(5)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以及社会危害程度有必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四、行政拘留与专门(矫治)教育的协调
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有关分级干预教育矫治体系规定,行为符合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要件时,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后,教育行政部门与公安机关可依职权决定将其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矫治教育。同时,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不法性的合理客观评价可能涉及行政拘留的适用。行政拘留与专门(矫治)教育二者间关系尚不明确。尽管目前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未成年人处以行政拘留后不予执行,但二者仍然存在同时作出与适用的可能,应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在检察意见中协调行政拘留与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
行政拘留与专门矫治教育措施均会产生限制未成年人人身自由的效果,但是行政拘留属于行政处罚中的一种,具有较强的惩戒属性,而专门教育制度属于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矫治的色彩更加浓厚。当对罪错未成年人适用行政拘留但不予执行时,专门(矫治)教育能够适当补强惩戒效果,二者并处也不违反“一事不二罚”的处罚原则,反而分别从惩戒端与教育端“双管齐下”地对罪错未成年人课以恰当评价或干预,充分体现“惩戒与保护并重”的特别司法理念。
五、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的界分与衔接
“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作为未成年人特殊梯级干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界分与差异尚不明确。目前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仅有原则性规定,一方面,需要通过立法实现规范补足与细化,另一方面,在规范缺位的当下有赖于司法实践予以界分。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专门教育”未明确体现拘束性等特征而偏向于纯粹的“行政性干预”,而“专门矫治教育”因体现明确的拘束性,且明确作为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情形的替代性措施,兼具“行政性”与“司法性”。“专门矫治教育”介乎刑罚与非刑罚司法处遇之间,具有更接近刑罚的干预强度。因此,检察机关在行刑反向衔接中应充分结合行为动因、家庭背景、悔过表现等多方面因素考量,差异化地适用“专门矫治教育”或“专门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助力推动“专门矫治教育”与“专门教育”间的分流与衔接,保证教育矫治效果落实。
六、行政处罚与专门(矫治)教育的检察监督
针对一般行政处罚,如出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处罚权或者不予处罚,以及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处罚程序不当等情形时,检察机关应及时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予以纠正。
涉及专门(矫治)教育时,检察机关应当依法能动行使检察权。由于专门学校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实施闭环管理,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剥夺罪错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检察机关应积极履职监督,确保这一具有人身拘束性的措施恰当与公正地实施。
一是充分利用“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同意”的前置程序。检察机关作为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组成成员之一,应当与其他单位一同充分协商探讨,共同评估专门矫治教育决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二是持续跟进,监督专门矫治教育的落实情况。如若发现教育行政部门与公安机关存在不当推进专门教育工作、专门学校矫治教育工作存在纰漏或教育行政部门等怠于履职的,应及时制发检察建议予以监督。
七、化解涉未成年人案件行刑反向衔接普遍问题
针对专门教育乃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必要时按照类案监督有关规定办理,发挥“穿透式”监督职能,适时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启动公益诉讼程序,以实现“治理一片”的效果。
其一,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在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中,发现行政违法行为类案监督线索和较为普遍的违法情形时,可以参照《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类案监督工作指引(试行)》有关规定开展类案监督工作;其二,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在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中,发现有关单位和部门存在违法情形或应当消除的隐患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向有关单位和部门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其三,充分依托未检业务统一集中办理的优势,在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发现公益损害线索的,及时提起公益诉讼。
八、建立行政违法记录封存机制
既有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规构筑了完备的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然而目前尚不存在法定的行政违法记录封存机制与之相呼应,一定程度上影响行刑反向衔接的治理效果。出于帮助罪错未成年人“再社会化”的目的,应借鉴《刑事诉讼法》中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将案件不起诉决定以及随后作出的行政处罚,包括接受专门教育或专门矫治教育的记录予以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