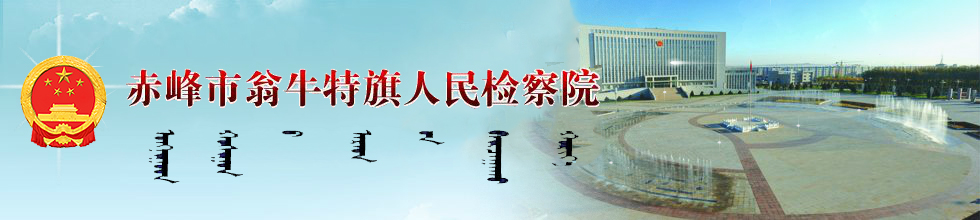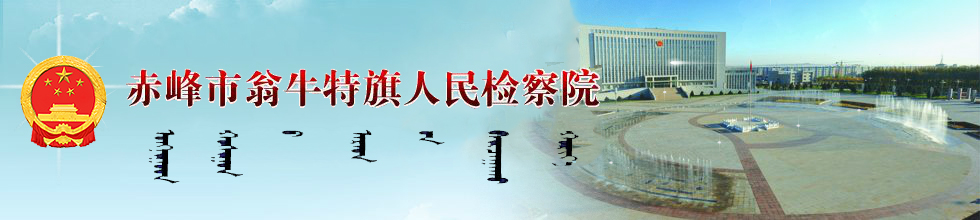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类型化的缺陷及理性回归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关保英在《江淮论坛》2022年第4期发表了《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类型化的缺陷及理性回归》一文。文章认为,《行政诉讼法》第25条对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列举规定,此种模式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是有问题的。推动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回归理性,需要作出相应的制度设计,包括对公益概念作法律上的阐释、对公益作抽象解释、对公益作概括规定、对公益作公众选择性处理、对公益由诉权主体作出判定。
一、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类型化的制度构型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表明,目前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在立法技术上有三个特点。一是对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进行列举规定。就是在浩瀚的公益范围之内列举规定了若干个公益范畴,通过列举规定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有了具体的内容、具体的范围;二是对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进行了主观分类。《行政诉讼法》有关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仅仅作了四或五个范畴的规定,但在这四个范畴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公共利益的范围;三是对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准公益考量。从这三个方面出发,《行政诉讼法》对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做出类型化的处理。这些类型包括:生态环境公益、资源保护公益、食品药品安全公益、国有财产保护公益、土地使用权出让公益。
二、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类型化的实践问题
《监察法》的制定以及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使我国国家权力体系和司法体制发生了变化,检察机关与行政系统建构了新的关系模式。但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类型化没有理性地建构检察职能和行政职能的关系,没有理性地使检察职能倒逼依法行政。从深层次讲,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类型化有下列实践问题。
(一)受案范围不周延性的问题
设计公益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行政诉讼保护公共利益,提升行政主体履行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职责的积极性。有关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与公共利益的对应应当是周延的和全覆盖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类型化以后,所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公益仅仅只有五个范围。类型化处理以后,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与公共利益的不周延便表现得十分明显,使得我国行政诉讼有关公益的救济无法落到实处。
(二)受案范围选择性的问题
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起步较晚,虽然受案范围的制度构型是由当下我国行政诉讼的实践决定的,然而,其采取的却是选择性的立法技术。这样的选择是一把双刃剑。在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采取选择性列举,其负面效果虽不能与选择性执法同日而语,但仍然是一个选择性的存在。
(三)受案范围问题应对性的问题
我国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型是由于公共利益中的敏感问题引起的。诚然,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应对有其必然性,但是行政公益诉讼应当符合法治的普遍化精神、系统性精神、结构性精神等。问题应对的方式作为受案范围有可能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但对一个理性的制度构造而言,问题应对的方式存在着固有的弱点。
(四)受案范围短期效果性的问题
两年的试点给人的感觉是案件井喷式的上升,而公众利益的保护是百年大计甚至是长久之计,我们更希望通过受案范围使行政公益诉讼和我国的行政诉讼一起构建起良好的行政生态,呈现长期的制度理性和制度效果。
三、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类型化的理论问题
从法理上讲,无论公益诉讼中的监督,还是公益诉讼中的公益都是一个种概念。作为种概念,它能够最大化地包容公共利益,能够最大化地体现监督的职能。而目前行政公益诉讼中的类型化则将一个属于种的概念,变成了属的概念,这显然不利于行政公益诉讼建构的初衷和其存在的理论基础。
(一)与受案范围由诉权决定的法治进步欠契合
2014年修订《行政诉讼法》过程中,受案范围是关注的焦点。立法通过诉权对受案范围做出框定,在《行政诉讼法》的第3条正式确立了诉权的概念。行政相对人行使着广泛的行政诉权,而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诉权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义务是相辅相成的。但目前《行政诉讼法》在公益诉讼中仅仅选择五个公益类型作为受案范围显然没有与由诉权决定受案范围的法治进步相统一,这是一个明显的理论困惑。
(二)与行政监督的全方位性欠契合
行政公益诉讼构建的理论前提在于,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行政公益诉讼涵盖于监督权之下,行政公益诉讼是监督权的转化形式。行政机关所有有关公共利益的行为都应当受到检察机关的监督,检察权每日每时都可以将行政机关处置公共利益的行为放在其视野之下。但仅仅五种类型的公共利益作为受案范围,使得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与受案范围没有很好地相适应。
(三)与公益保护中公益的本质欠契合
《行政诉讼法》所保护的公共利益是一个周延的、全覆盖的公共利益。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公益肯定是一个规范化、全方位和覆盖方方面面的公益。目前类型化的受案范围使得行政公益诉讼与公益保护的本质还不够契合。
(四)与法治的三位一体机制欠契合
全面依法治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有机统一。三位一体中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法治社会是依法治国的最高标准,而法治国家是依法治国的最终目的。目前我们所选择的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实质上豁免了行政系统大量的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和在公共利益面前不作为行为,这实质上是没有理性地处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关系。
四、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回归理性之路径
《行政诉讼法》有关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显得比较单薄,目前在《行政诉讼法》中有关公益诉讼的规定只有一个条款。关于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完善,试提出下列思路。
(一)对公益概念作法律上的阐释
《行政诉讼法》将公共利益二分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尽管该规定首先将公益的范围框定在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中,然而国家利益包含哪些内容,社会公共利益包含哪些内容都是不确定的。这就需要我们从法律上对公益的概念进行阐释,排解争议。通过相关的法律界定概念事实上是完全可行的。目前《行政诉讼法》给人的错觉是公益仅仅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等个别范畴。依法界定公益是公益诉讼理性化必须做的工作。
(二)对公益作抽象解释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构建是百年大计,如果从更高的站位考量,可以说列举式公共利益的弊大于利,通过列举规定是不明智的做法。因此在受案范围的确定上应该对公益做抽象解释,一个利益是否为公共利益应当由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决定、应当由行政相对人决定,而列举规定的诸范畴基本上剥夺了相关主体对公共利益的自行决定权,最终获益的是对公共利益造成影响的行政主体。
(三)对公益作概括规定
公益诉讼中的公共利益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范畴,仅仅列举其中的几项利益既不科学又不明智。鉴于目前我们对行政公益诉讼的认知,可以将概括规定与列举规定结合起来,但要对概括规定作进一步的细化,避免仅仅用一个“等”字予以表述,造成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困惑。
(四)对公益作公众选择性处理
就行政诉讼的制度构型而论,实质性的问题在于我们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将有关的公众诉求纳入救济的轨道,通过司法审查将公共权力尤其行政权置于司法的监督之下。从这个角度讲,公共利益既不需要由行政权进行选择,甚至也不需要司法机关进行选择和干预,而应该将选择权归于公众。如果一个利益引起了公众的普遍关注,成为了某种舆情、成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公众诉求,就应当定性为公共利益。该理念在操作层面上虽有难度,而无须证明的是,它是公共利益判定的最为本质的利益,最能够通过它确定公共利益的路径。
(五)对公益由诉权主体作出判定
既然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处于主导地位,有关公益的判断就应当交给检察机关,行政相对人可以对检察机关做出诉求,而某一公益诉讼是否进入诉前程序或者进入完全的诉讼程序都由检察机关作出判断。应当将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公诉人,其作为公诉人的身份就有权对什么是公益诉讼的案件、什么不是公益诉讼的案件作出权威性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