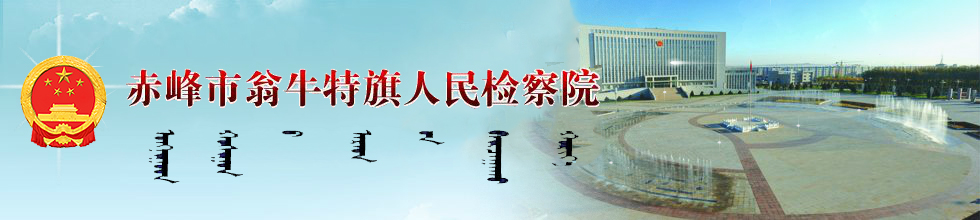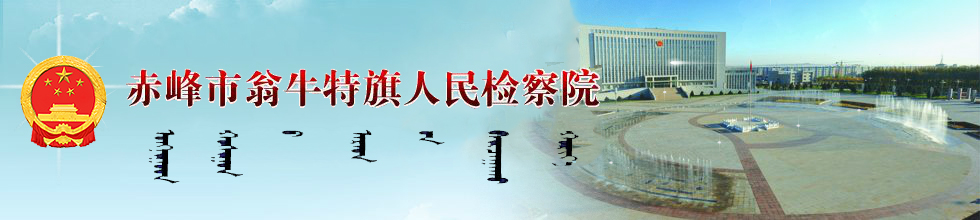巡回检察视角下刑释人员重新犯罪问题研究
丁子明* 阳志刚*
近年来的江西乐安入室行凶案、北京摔婴案、河南公交车杀人案、云南通海灭门案等恶性案件,作案人均为刑满释放人员,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无疑给我国监狱的刑罚执行制度敲响了警钟。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社会和谐稳定、人权保障、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需求更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监狱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也是国家内部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刑罚执行和监管改造质量直接关系到刑罚目的能否最终实现,也直接关系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全面落实和社会的安全稳定。对监狱而言,已不再满足于不跑人不出事和落实刑罚惩戒功能,而要更加关注改造的实际效果。对检察机关而言,我们要通过巡回检察加强对罪犯教育改造活动的监督,查找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分析这些刑释人员铤而走险的原因,以期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的调研基本情况
在罪犯出入监专项巡回检察中,我们对Z市看守所2018年至2020年交付监狱执行的1376名罪犯进行了数据统计和摸底(见图1),重新犯罪人员为457名,约占交付监狱执行总数的33%。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刑释人员重新犯罪具有3个主要特点。
|
年份 |
送监人员中
重新犯罪人数 |
暴力型和涉财产型犯罪 |
共同犯罪 |
涉黑涉恶犯罪 |
|
人数 |
占比 |
人数 |
占比 |
人数 |
占比 |
|
2018 |
138 |
130 |
94% |
44 |
32% |
13 |
9% |
|
2019 |
151 |
135 |
89% |
53 |
35% |
16 |
11% |
|
2020 |
168 |
150 |
89% |
48 |
29% |
24 |
14% |
|
合计 |
457 |
415 |
91% |
145 |
32% |
53 |
12% |
图1.Z市看守所2018-2020年送监执行重新犯罪人员数据统计
(一)犯罪类型以暴力型和涉财产型犯罪较为普遍,部分为共同犯罪
根据对457名重新犯罪人员罪名的统计(见图1),发现有415人系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强奸、非法拘禁、聚众斗殴、敲诈勒索、诈骗、贩毒、盗窃等暴力型和涉财产型犯罪类型,占重新犯罪总数的91%。系共同犯罪的145人,约占32%。从近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现,部分社会上的黑恶势力把刑释人员作为团伙成员的重点物色对象,此次统计的涉黑涉恶类重新犯罪人数约占总数的12%。从上述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重新犯罪人员的犯罪类型为暴力型和涉财产型,共同犯罪的约占三分之一。
(二)犯罪主体以城市无业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为主,文化程度高低与重新犯罪人数呈反比
经调阅档案发现,457名重新犯罪人员中,有419人为城市无业人员或农村务农人员,约占92%;此外,个体工商户14人、进城务工人员13人、企事业单位职工11人,共占8%。从文化结构来看,初中及以下文化层次369人,约占81%;高中或中专文化层次66人,约占14%;大专及以上文化层次共21人,仅占不到5%。由此可以看出,刑释人员文化程度越高,重新犯罪人数越少,无业和务农人员重新犯罪率较高。
(三)犯罪时间以刑满释放后一年内最为高发,之后呈逐年递减趋势
司法部曾对全国刑满释放3年内重新犯罪的7132人进行调查,发现刑满释放后第一年内重新犯罪的占48%,第二年重新犯罪的占32.2%,第三年重新犯罪的占19.8%。从本次对457名重新犯罪人员出监后重新犯罪的间隔时间分析,其中有238人在刑满释放后一年内重新犯罪,约占总数的52%;135人在第二年重新犯罪,约占30%;65人在第三年重新犯罪,约占14%;三年后重新犯罪的19人,约占4%。从上述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重新犯罪率随时间的推移呈递减趋势。
二、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的原因分析
我们通过组织并参加10次监狱常规、专项、交叉巡回检察,采取现场查看、问卷调查、个别谈话、调阅档案、查看资料、分析数据以及走访部分刑释人员等形式,对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和分析。重新犯罪是多因一果的产物,除了人格因素外,社会诱因和监狱改造质量也是重要因素,而且各种原因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具体来说,可分为个人、社会和监狱三方面的原因。
(一)个人道德感缺失、法治观念淡薄、文化层次低、缺乏谋生手段
一是人生观扭曲,道德感缺失。人生观是人们对于人生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在人的主观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到人的整个精神风貌,决定其如何处事待人。错误的人生观是重新犯罪的内在动因。在巡回检察中,经查看资料、个别谈话发现,大多数重新犯罪者有不正确的人生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贪图享受而又好逸恶劳是其主要表现,有的重新犯罪者具有反社会性,无视社会公德和法制,对社会不满,充满敌意,其行为得不到良好的调控,从而重新犯罪。二是法治观念淡漠,对刑罚缺乏敬畏感。在巡回检察中,经个别谈话、问卷调查、调阅档案发现,大多数重新犯罪者都心中无法,普遍视法律为儿戏,有的是明知故犯,故意去破坏法律所维护的正常社会生活秩序。他们没有从内心认罪服法,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怨天尤人,产生报复社会的想法。部分罪犯思想深处对刑罚缺乏敬畏感,具有强烈的蔑视法律心理和侥幸逃脱法律制裁心理。三是文化层次较低,没有一技之长。在重新犯罪的刑释人员中,初中及以下文化层次的占绝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导致这些人认识能力不高,分辨能力差,自控力、意志力都较薄弱,缺乏自制和自信,也没有健康向上的人生追求。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问题,他们由于长期脱离社会,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脱节,特别是在当前社会转型期,求职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而大部分刑释人员文化程度低,在监狱改造中又未能学会一技之长,因此陷入无业可就和有业难就的困境,生活没有保障。在生存都成问题的情况下,他们一有机会就重操旧业,靠贩毒、盗窃、抢劫、诈骗、敲诈勒索来谋取自己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源。
(二)社会帮教效果不佳、社会歧视以及不良旧环境
从社会诱因方面来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社会改革期,社会剧变中,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贫富差距、家庭、人口、公众态度、公共舆论、司法等都可以成为重新犯罪的诱因。一是社会帮教措施没有得到有效落实。我国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已有多年,并初步形成了针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管理体系。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地方政府对安置帮教工作重视程度不同,导致帮教效果存在差距。一方面,部分刑释人员为了生存和发展,离开原居住地到外地打工或寻求发展机会,导致帮教工作脱节,帮教责任分散;另一方面,对帮教对象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困难了解、关心不够,影响了帮教效果。一些刑释人员走入社会后便无人再进行帮教,在失去监督约束、缺少温暖关怀的情况下重新犯罪。二是社会歧视。由于罪犯“标签”的影响,社会上很多人对刑释人员持有偏见,人们往往将犯过罪的人简单地归为“坏人”,对刑释人员不信任甚至敌视,视他们为“异类”,一些单位在招聘中明确不招收刑释人员。刑释人员的子女等近亲属在就业等方面也存在受牵连的现象,这些歧视使刑释人员的生活和工作都处于不利境地,被社会边缘化,甚至丧失了重新做人的信心和勇气,从而自暴自弃,重新犯罪。三是不良旧环境的影响。刑释人员在狱中常常会认识一批“狱友”,他们在语言、心理、价值取向、需要满足等方面容易形成一致,犹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言,人有归属和爱的需要。刑释人员在面临着如社会歧视、家庭拒绝、同伴疏远、就业困难等多重压力和困扰,加上本身的自卑心理,很难融入其它正常群体,这往往导致其为了寻求所谓的安慰和支持,加入在狱中认识的旧狱友群体中,以此满足其心理归属的需要。在此类群体中,刑释人员很容易受到不良旧环境的影响,走上共同犯罪道路。
(三)监狱对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不高
把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是我国监狱工作的根本宗旨,教育改造作为改造罪犯的三大基本手段之一,在监狱工作中无疑应处于最核心的位置。但在实践中,我们通过对3个地级市4所监狱开展巡回检察发现,监狱教育改造职能未能得到有效落实。一是监狱存在“重生产轻改造”的情况。我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监企合一的制度,监狱既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又承担着企业生产的功能。虽然自监狱体制改革工作推进以来,实行了监企分离,但经巡回检察发现,监狱仍未能改变和企业“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运行现状,仍未真正从搞经济、办企业的窘境中摆脱出来,尚未将监狱民警从每天繁重的生产任务中解脱出来,这势必导致监狱强化劳动改造,弱化教育改造。在实践中,超时劳动,劳动时间占用学习时间和休息时间成普遍现象;在对罪犯考核时,同样以其创造多少劳动成果为重要依据,劳动改造的目的由此被淡化,甚至于造成罪犯厌恶劳动的后遗症,罪犯改造质量也相应得不到保障。二是监狱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课程单一。在巡回检察中发现,各监狱严重缺乏教员、教材、教具,实际教学内容与教学计划安排不一致。在罪犯思想、文化、技术教育方面,未严格按照司法部《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司法部令第79号)给成年罪犯每年安排不少于500个课时的学习、未按规定开展扫盲教育、无技术教育教案或教案较少、教学课程单一,多以观看视频教育片为主。在罪犯个别教育方面,没有根据罪犯的思想状况和动态,有针对性的采取个别教育改造措施,主要体现在与罪犯的个别谈话记录基本雷同、内容以询问基本情况为主、无实质性的谈话内容、罪犯心理矫治流于形式。在罪犯出监教育方面,未对即将刑满的罪犯进行时限三个月的集中出监教育,存在以会见代替社会帮教的问题。三是罪犯学习时间得不到保障。通过巡回检察,我们发现各监狱均未按照司法部《关于加强监狱安全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司发电[2009]第91号)落实“8511”制度,即每周5天劳动教育,1天课堂教育,1天休息,罪犯每天劳动时间不得超过8个小时。各监狱普遍只在每周教育日安排半日学习,另外半日安排劳动,在罪犯基本的学习时间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教育改造质量和效果无疑大打折扣。
三、预防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的对策
预防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笔者认为需要从监狱体制、民警队伍、罪犯教育、社会力量支持、刑事奖励制度、安置帮教等六个方面多管齐下,全面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对检察机关而言,就是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通过巡回检察手段,集中精力查找解决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与监狱管理部门共同研究提升教育改造质量之策,最终实现法律监督和刑罚执行工作的双赢,以具体行动落实好国家总体安全观。
(一)监督监狱落实体制改革,改变“重生产轻改造”的现状
2003年司法部提出逐步实现“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监狱体制改革总目标,2008年以“监企分开”为重点的监狱体制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目前,监狱体制改革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改革进入深水区,也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检察机关应当通过巡回检察“以查促改”,为继续深化推进监狱体制改革提供检察动力。笔者认为,改变监狱“重生产轻改造”的关键是要健全监狱经费支出全额保障机制,解决监狱的后顾之忧。在此前提条件下,将企业职能从监狱分离出来,从管理体制上做到与监狱完全脱钩,从而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样才能将监狱从搞经济、办企业的窘境中彻底摆脱出来,才能使监狱民警从繁重的生产任务中彻底抽身出来,才能充分发挥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的功能作用。
(二)监督监狱开展罪犯分类教育,提高教育改造质量
检察机关应当监督监狱落实罪犯分类教育,根据刑事个别化原则“因材施教”,针对暴力型、涉财产型这两大类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率最高的罪犯,科学开展分类教育。这类群体如果没有改造好,将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安全稳定,监狱民警在管理教育这类罪犯的时候,不仅要确保监管安全,更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起改造好罪犯就是保社会安全的意识,着力在改造思想、净化心灵、矫正恶习上下功夫。要开展犯因性分析,了解其人格特点和犯罪原因,做好心理矫治工作,加强普法教育,让他们变刑期为学期。同时,要在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基础上,拓展职业技术教育,根据社会需求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为罪犯刑满释放后正常就业谋出路。
(三)监督监狱严格依法假释,推动符合的罪犯提前适应社会
本次调研数据分析表明,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后重新犯罪率随时间的推移呈递减趋势,这说明他们需要一个过渡缓冲期才能够适应社会,而假释考验期的设置就相当于一个过渡缓冲期。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假释适用率明显偏低,除上海、青岛等城市外,大部分省市保持在2%左右。2016年全国假释率为1.28%。而在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假释适用率分别达到了48.4%和20.9%。即使在亚太地区中,我国比斐济、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略高一些,处于倒数第四的位置。这充分说明,我国以假释制度作为刑罚的调节阀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随着社区矫正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规范化,假释的行刑效果会更加有保障,将更有利于促进罪犯重新融入社会。检察机关应当监督监狱严格依法假释,从而对符合的罪犯假释,促使罪犯提前适应社会。
(四)推动构建“一体化”刑释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机制,做到管理信息化、安置市场化、帮教社会化
提高刑释人员安置帮教工作质量,是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的重要措施。对刑释人员的安置帮教是一项系统化的社会工程,目前吉林省已实现了全省刑满释放人员衔接、安置、帮教一体化,建立了358家过渡性安置基地——“彩虹基地”。全国各地也相继建立了各种刑释人员过渡性安置基地。笔者认为,做好刑释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将工作落到实处。一是管理信息化,从中央到地方要层层建立和健全安置帮教工作的组织网络,建立刑释人员信息管理系统,进一步理顺监狱、公安和司法行政职能部门的工作关系,实现无缝衔接、合理安置、信息共享。二是安置市场化,要有针对性的对刑释人员开展就业培训,通过设立社区公益性岗位实现托底就业,并建立过渡性就业基地、协助自谋职业、鼓励自主创业等多渠道开展安置工作。三是帮教社会化,要积极调动社会资源,将帮教工作融入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有关环节之中,在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下做好帮教工作。